新闻•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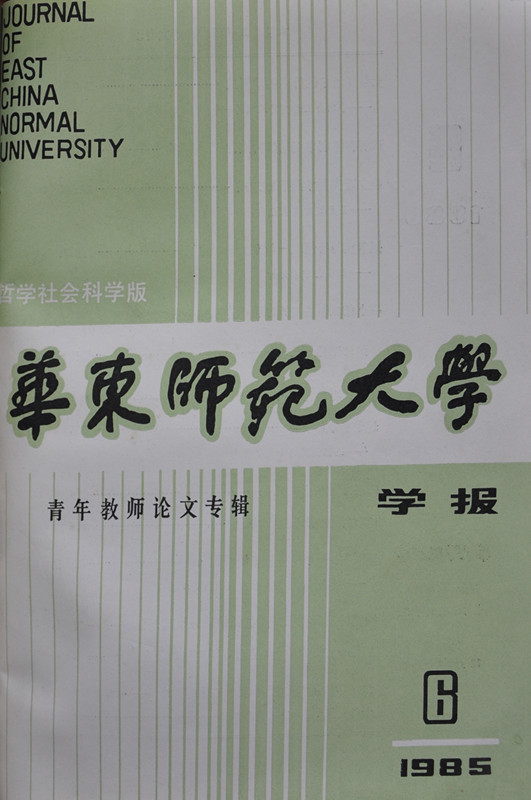
乍暖还寒的初春,走在华师大中山北路的老校区。大量的学生已经搬去闵行新校区了,这里相对有点冷清,除了穿梭的车辆不断。草木待发,共青路两旁阴翳蔽日的法国梧桐也还光着枝桠。但毕竟杨柳风起,吹面不寒了,丽娃河亦春水如蓝。一个朝气蓬勃的季节,正在积蓄能量,等待绚烂这个世界。这次要参加的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与学校社科处共同主办的“学术·未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研究者学术思路研讨会”,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应景的会议,会议的主题——青年,不正如眼前的季节一样,敏感、美妙、喷薄欲出吗!
30年前,华师大学报曾经推出国内第一个“青年学者专号”,当时的中文系讲师王晓明在《过于明晰的世界——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中,将对中国20世纪文学历史局限性的沉思与现代著名作家创作道路的研究有机结合,独辟蹊径;政教系讲师陈卫平在《确立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论严复对发展近代科学的哲学思考》中,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透视我国先哲对发展近代科学的思考,令人感触。而今,当时的青年学人,如陈兼,现已成为美国乃至国际二战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又如专号中的童世骏、陈克艰、夏中义等,几乎都已成为国内甚至国际相关学科的代表性人物。
当年专号特别配发了以《青年学者的‘现在’与学术刊物的使命》为题的编后记,当中这样写道:“注意新观念、新方法、新问题,在学科的互渗中摸索,在科学的继承中前进,这是当代青年学者的一个特点……或曰:青年学者思想不成熟。确实,他们的学术思想刚刚生长发育,每每有阙漏与抵牾,然又何足为怪,对思想理论而言,绝对的圆满只能是‘圆寂’的同义语;何况,科学进步、理论发展的动力除了直接来自理论与现实的经验不一致外,还常常是来自理论与理论的差异……正是由于有了理论之间的对比,才得以提示人们去深究已有理论的适用度,无各种‘不成熟’思想的诞生,这理论之间醒目警心的‘对比’和‘差异’将很难说起,仅就此而言,青年学者的探讨也应予肯定……”
对一所高校来说,青年工作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关系到学校的未来。对一个国家而言亦是如此。青年理所应当受到格外的重视。然而,今天多元社会中的青年却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巨大的压力。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状况并不如他们的职业听起来那样光鲜。犹记一年前,也是三月,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张哲挥别人间,分别是36岁和37岁。两位才俊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人当青年,如何行路”,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也是高压人群,生活和事业上都存在诸多的困境,急需关注和关怀。与此同时,青年人才的青黄不接的现象也很显著。60、70后的青年学者能否稳稳地接住40、50后学者手中的学术接力棒,且更好地传承下去,在整个学术界都是普遍的问题。也正是在加速推进青年教师队伍发展的战略之下,师大学报哲社版编委会决定于今年下半年再次专门出版“华东师大学报青年学者专号”,并配以论坛和评奖,向国内外学术界隆重推介一批该校今天的青年学者。这一举措意义重大。
士志于道,学以致用。时迁代移,不同时代的知识者面对的现实问题迥然有别,学术思路自然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学者刘擎敬告年轻教师:30年之后看当年那些论文题目,似乎感觉并不突出,但是如果回头看80年代中期的研究背景的话,当年那些年轻的学子是相当专业的,他们的文章有深厚的思想内涵。李泽厚称那是思想家凸现的时代。因此,现在看来波澜不惊的题目在当时其实是具有很强的先锋性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才能发现它的价值。在当下学术已经过度专业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时代,我们不能失去对大时代精神的把握。如果说,在80年代思想激荡的时候,要突出学术专业话语的前卫,那么在非常专业化的当下,学术则要突出其思想关怀,突出跟我们的处境是相关的。
一言以蔽之,青年学者要在大时代下面思考问题。此次会议集聚了该校三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五十余条研究思路,从“突发事件政府应急话语技术与形象修复策略研究”、“晋唐间的中华意识与‘中华’再造”、“利益受损农民工的维权行动以及与政府之间互动的研究”等选题,可以欣喜地看到这些年轻教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的自觉。学报主编胡范铸教授表示,为紧扣当下社会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学报也拟加重对“国家治理”的探讨,期待青年学者的加入。“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虽然要为稻粱谋,但学术,乃国家公器,绝不能孜孜以个人利益为念。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青年学者的学术使命感尤其珍贵。
一段时期以来,在社会浮躁的氛围中,在急功近利的学术衡量标准下,学者庸俗化倾向加剧,学术理想丧失,学术信仰畸型,价值观被扭曲,我们的知识界被广为诟病。要想改变这种扭曲的现状和形象,必须要从今天的青年知识者的培养着手。我们不缺乏天才,缺少的是培养天才的土壤。师大学报此举正是化学刊为肥沃的春泥,为学术的未来培土护花。若将青年学者比作千里马,学刊曾热切地扶助过一匹又一匹尚在踉跄、蹒跚时的幼驹。如果说学报30年前着眼于青年的“现在”,30年后更寄望于学术的“未来”,此等胸襟与关怀,于学术的良性发展,于青年人才的成长,善莫大焉。我们的学术太需要这样的春泥,这样的伯乐。30年前专号的编后记这样结尾:“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未来生长于现在。历史观与辩证法应当统一起来。”这段充满力量的文字,今日读来仍然掷地有声,仍然振聋发聩。中国学术的未来在于青年,全社会都应该珍视青年,为青年的成长提供助力。同样,青年学者也要独立为学和思考,致力创新,勇于任事。如此,文化复兴,未来可期。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电化教学楼五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电化教学楼五楼 邮政编码:200062
邮政编码:200062 业务咨询专线:
业务咨询专线:


